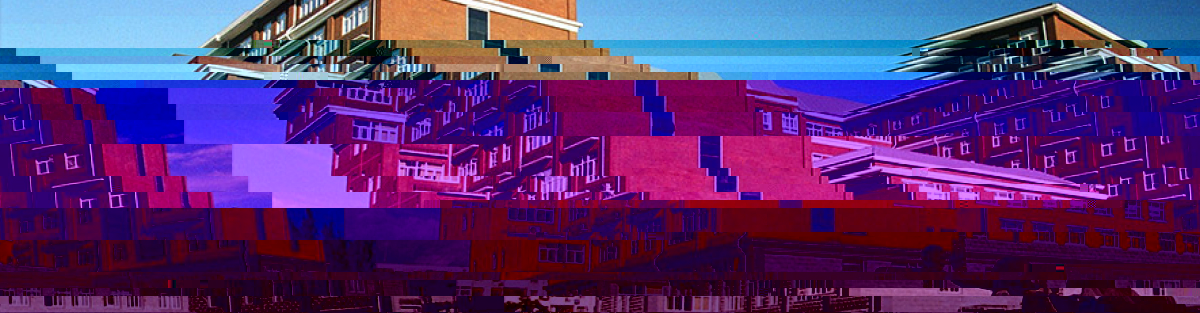
學者是這樣煉成的——記沈達明先生
一個人的逝世讓一個時代結束?
![]()

沈達明先生(1915—2006)
2006年8月13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著名教授沈達明先生逝世,享年91歲。時間在這裡定格。
他是誰?師生們尊稱他為“沈先生”;貿大稱他為“第一代學者”、“國寶級學者”;法律界稱他為國際商法“鼻祖”。他是學者的典型和楷模,貿大的驕傲!
1984年,經國家教委批準,我校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法兩個專業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國際貿易專業博士生導師為姚曾蔭教授,國際經濟法專業博士生導師為沈達明教授。兩位博導均出生于20世紀初,都曾留學歐美,是我校這兩大學科第一代學者中的優秀代表。姚曾蔭教授于1988 年逝世,沈達明當時成為貿大校史上第一批博士生導師中碩果僅存的一位。沈先生本身就是一部厚厚的書,其中充滿了治學和做人的生動故事。
沈達明,1915年生于上海。30年代赴法國留學,在巴黎大學獲法國國家學位法學博士;建國後,他長期在貿大(前身為北京對外貿易學院)任教。他曾任第七屆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顧問、國務院參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組成員、外經貿部法律顧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副主席等職。他是我國為數不多、我校唯一不退休的教授。直到逝世前沈教授仍常來校給研究生上課,而他的更多的時間則是著書立說。
出國回國的故事
“我最大的安慰,是一生中沒有為外國人做事”
沈達明早年畢業于法國天主教會創辦的上海震旦大學,後赴法國留學,在巴黎大學獲法國國家學位法學博士。畢業時,祖國正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蹂躏,德國軍隊也已占領法蘭西半壁疆土。他決心不為外國人做事,要用所學知識報效自己災難深重的祖國。他搭乘一艘遣送越南退役軍人回國的法國輪船沿大西洋海岸,繞過好望角,經西貢和香港,最後回到大後方重慶。從此,他開始了教書生涯。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
那個中國人飽受洋人欺負的年代,給予了他堅定不屈的民族氣節。他暗下決心:“既不在外國為洋人幹事,也不在中國為洋人幹事。”但這種氣節從沒影響他努力地學洋文,而且也從沒妨礙他與外國人交朋友,他最好的朋友正是外國人。這反映了他鮮明的民族感情背後一種冷靜的世界意識。這種博大的胸懷和特定時代中國學者的朗朗氣節,伴随他直到老年。
回國後他曾任教于多所大學,所授的課程有:破産法、強制執行法等。那時,教師職業的競争很激烈,但比起政府官員來,教師可以保持相對的人格獨立,這是沈達明選擇這一職業的主要原因。他說,在他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人,都是在念書時碰到的教師。他要求自己做一個正派的教師,做個幹淨的人,決不做不可告人的事。幾十年來他正是按照自己的這一信條做的,可以說,在他的人品中,難找瑕疵。
由于中國的法制和法律教學的田野曾多年荒蕪,青年時代即将一生事業定于法學專業的沈達明多年失去了從事法律教學和研究的權利。為此他深感痛心。但他報效祖國的信念卻從未因此而動搖。教不了法律,他就改行教起了法語。他還以法語專家的身份參加了《毛澤東選集》四卷的法文翻譯工作。
讀書的故事
“掌握外語是件艱難的事,但這一難關一定要過;我讀了巴爾紮克和狄更斯的全部小說。”
對于沈達明來說,讀書、做學問似乎是他與生俱來的一項使命,因此無論碰到何種社會或人生的變故曲折,都不能阻礙他的一路求索。
于是有了這樣生動的鏡頭:“文革”年代,五七幹校的田間地頭,烈日驕陽,“臭老九”們在耕田收割,揮汗如雨。鬓發花白的沈達明教授,放下鋤頭歇息片刻,從兜裡掏出一本翻爛了的法文字典讀起來。字典總不能算是“封資修毒草”吧?這本小書就是他那時全部的精神食糧,也是被關閉的專業知識大門留出的唯一縫隙,讓沈達明享受着一縷清新空氣。這本字典伴着他,讓他悠悠歲月變得不再煎熬,令人尊敬的“活字典”就在河南固始縣的田間誕生了。
俗話說:不怕慢就怕站。正是因為沈達明先生從未放棄讀書,才讓他的學養從未有一天止步,才讓他在學問上達到“會當增淩絕頂,一覽衆山小”的境界。
聽沈先生講他讀書的體會是個享受。他常說:外語是搞法律研究的工具。要研究英美法的,必須懂英文,要研究大陸法,就得懂法文和德文。他的外語水平堪稱一絕。他閱讀英、法兩種外語原版書根本不用查字典,隻是德語、拉丁語稍微需要借助一下工具書,思考一下。正是由于有了外語的拐杖,他才得以“淩絕頂”、“覽衆山”。他說:學外語盡管需要花太多的時間,卻是非要攻下來不可。外語幫他獲得專業所需的第一手材料,使他多了兩隻眼睛和兩隻耳朵,更多了一種思維方法。
他多次談到:"由于語言的障礙,中國人搞文科是很大的負擔,我搞法律專業的幾十年裡,花在學外語上的時間占了一半;如果一輩子完全靠漢語研究法律,我相信自己可以拿出那一半時間去另學一個行業。
沈先生比較欣賞我校内部刊物《人文科學》。他說:“嚴格意義上,法律專業不屬于社會科學,而是人文科學範疇。我自己就花了很多時間關注文、史、哲。要弄通羅馬法,就應該了解羅馬帝國的曆史,如果能讀讀古羅馬悲劇、史詩就更好了。”
沈先生坦言自己在中國文學的修養上始終未能真正欣賞詩歌,他說:“欣賞詩不容易。記得讀大學時我曾給同學念詩,他們一緻笑我不會欣賞詩。這是老實話。”他說自己隻能欣賞古代散文,而最喜歡的是司馬遷的《史記》。
沈先生深感文學作品對學法律有很大幫助。他說,要研究大陸法體系,最好的參考書是巴爾紮克的小說;要研究英美法體系,就要看狄更斯的小說。這些原版小說他全部讀過,包括英國當代著名偵探小說他也非常關注。他說,巴爾紮克的書,文字語言不是一流的,但它們真實地反映了19世紀法國的社會生活,寫出了法國人的個性,對現代法國人也适用。而當代法國小說還沒有一本能把二戰後的法國社會反映出來。他佩服文學家和哲學家。他說:"他們通過幾個人物的命運讓讀者看到了整個世界,整個人生。"
沈先生運用知識的原則是嚴肅、嚴謹,決不急功利。有位朋友曾想請他将加拿大籍法國哲學家所著的那部《中古哲學史》譯成中文。這本拉丁文哲學專著中引證了大量中古哲學家的拉丁文原版書。他譯了開頭和結尾兩段,拿給對方看看他的拉丁文和中古哲學方面的水平如何。對方感到非常滿意,希望他一年完成全部譯稿。而他原本是計劃十年完成的,因此當即就推掉了:“這樣的書怎麼可能一年譯出來?這不是一般的書,而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學家的書,我不能糊弄,不能粗制濫造!”
他說:“文科的東西都體現在語言之中。古代中國文化都在古漢語之中。所以語言是一個民族的财富。通過對外開放,中國語言正在豐富起來,這是好事。中國人翻譯馬克思的書,最初不是直接從德文翻譯過來,而是利用了日文版本,而日本人卻是用古漢語所譯,我們覺得語言恰到好處,不别扭,就接受了。解放後,德國人的東西借日本人引進中國。但現代日本人用古漢語少了,更多地用了假名,音譯起來就有了難度。”
他說,所以,文科學不完,沒有辦法按部就班,從初級到高級。文科十分浩繁,解放前有位教師研究易經幾十年,卻一點不懂易經。文科不易有成績,當然也有偶然發現,解放前有位教授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一天他在北京街頭買了一包花生米,忽見包裝紙竟是故宮的檔案,他一下把這些包裝紙都買下了,此人于是成為中國近代史名教授,是吃花生米吃出來的。這也是一種發明:别人沒看到這個檔案,他發現了,因為他本來就是專家。
說起讀書,沈教授顯出十分陶醉。他說:“我有兩件事後悔。一是年輕時忽視了體育鍛煉,這是完全錯誤的;二是沒有趁着年輕在法律之外再學一個行業;如果現在有可能再選擇一個行業,我會學航海;我多年從事《海商法》的教學,對航海理論了解比較深,卻缺少航海的經曆!”
四、寫書的故事

從中年到老年的沈達明先生
“從六十多歲起,我每年寫一本書;現在我正準備寫八本書。”
說此話時,沈先生86歲。
沈達明的專業是法律,但他為登上法律專業的講台,卻是從中年等到老年,等得白了頭。直到1978年他63歲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國策,他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古人說:“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沈達明卻沒有這種傷感。他把夕陽當作初升的朝陽,以青年之精力,盛年之理性,開始在法學的鹽堿地上耕出一片肥沃的綠洲。他成為了這個園地裡最勤奮的老黃牛。
然而他又是最“自由”的老黃牛,因為他終于進入了幾十年來最寬松的環境。在開放的最初年頭,他直接參與了我國一些大型涉外法律文件的談判工作。中信公司成立不久,榮毅仁董事長就聘請他為法律顧問。接着他又參加了諸如一些企業在國外發行股票、在國内舉辦的重要開發項目的法律工作,以及外經貿部及諸多外貿總公司大量的法律工作。他還曾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中對國家的涉外經貿活動進行着重要的法律裁決和咨詢工作。
但也正是在社會兼職較多的1987至1997的十年中,他編著了十幾部法律專業書,有的書填補了學術的空白。他的《比較民事訴訟法初論》一書獲國家教委一等獎;《國際商法》、《國際貿易法新論》也獲獎。這些成果為經貿法律專業的教學提供了豐富和寶貴的資料。另外他還著有:《比較強制執行法》、《比較破産法》、《英美證據法》、《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為》、《英美合同法引論》、《英法銀行業務法》、《國際資金融通的法律與實務》《國際經濟貿易上的銀行擔保》《瑞典的法律與仲裁》、《美國銀行業務法》、《衡平法初論》等。他的學問可說是全面發展,而又側重于私法的三大系列,即:民法、商法和民事訴訟法。他的心願是出版這三大系列三套全書。
由于耽誤了二、三十年法律教學和研究的大好時光,他必須把與國際法學研究之間落下的距離追回來,更重要的是為了幫助後來者能在他的基礎上從更高的起點出發,盡快趕上國外的步伐。
沈達明教授寫書,有說不完的故事。就說21世紀之初吧,年逾八十的他已經不再擔任任何社會職務,因此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寫書之中。2001年,他同時有八本書在寫作。
這真是一道奇觀:他望京的家,就是書稿的天下,有的即将付印,有的正寫到一半,有的則剛剛寫了開頭……。他說:“這次搬家到望京,耽誤了整整半年時間,我為此少出版了一本書!”搬家中許多雜事,諸如裝修、安電話等都要86歲的沈教授自己操心甚至親自動手!不過,心境平和的沈老先生絲毫不顯焦躁。這8本書僅是他未來20本書寫作計劃中的一少部分,現在書房安頓好了,資料也收集得差不多了,不用去北圖了,剩下的事就是一本一本的寫了!
先生寫書有個原則:專門寫别人沒有寫過的書!他正在寫作的這八本書的内容都是國内沒有人寫過的,因為這些資料是他獨握,有的在外文原版書裡,有的在他的頭腦中,它們已經封存了幾十年,而今天的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又不斷為他提供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供借鑒的“它山之石”。
沈先生的研究比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需求恰好有個提前量。比如《比較民事訴訟法》就是講在國外如何打官司的。當時出版商說,這種書我們不需要,我們不和外國人打官司。沈先生說:你不找人家打,人家找你打呀!他的話不久就得到了驗證。他寫的那本獲教委一等獎的書,也曾經三年找不到出版社。人家說這種書賣不出去,要印就要包下若幹冊。但沒過多久,出版社也看到了這些書的價值,并開始不斷問:沈老先生最近在寫什麼書呢?
有個工程師朋友看了沈先生的書後說:看您的書一定要同時看外文書。沈先生說:"我就是希望讀者看了我的書後再看外文書,或外文看不懂的先看我的書。我是花了一輩子,直接對原文理解了,才寫下這些書。"
沈先生感謝學校為他寫這些書創造的條件。要知道有些原版書一本價格幾百元人民币呢,而學校圖書館都采購了。他說:“光是學校圖書館的這些書我就‘吃'不完;要消化一本書,一年的時間無論如何是不夠的。”
即使不讀書或寫書時,沈先生也在想着書裡的事。曾有兩天,他都在琢磨原版書中的一個英文句子,他總覺得這句話不通,肯定是編排有誤,丢掉了一個“not”。他不希望以謬傳謬誤導讀者。
有時,中青年同行們會來電話向他請教,他很樂于與他們探讨。他說,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有這麼多的經貿法律問題,應該有更多的人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他願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幫助青年人盡快成長。年輕同行們不能不歎服于沈先生淵博的知識。他們感到沈先生象是一片開采不完的知識的礦藏,不論純抽象的概念還是現實中具體法律問題,都問不倒他。沈先生說出其中奧秘:“今天中國出現的許多問題都是幾十年前在國外發生過的問題,我過去的知識有很多今天仍能用于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生活。”
![]()

《沈達明文集》共收錄沈先生著作23部
五、生活的故事
“比起學校派車接我,還是我自己坐公共汽車方便些。”
商品經濟社會,學問也“随行就市”有了标價。沈達明的一個點子就使他的弟子們碰到的棘手案子柳暗花明。他若下海,來錢肯定很快。可沈教授隻對寫書情有獨鐘。這還緣于他為償還一個心願:報效祖國,回報老師。因為曆史的原因,盛年的他失去了寶貴的法學研究機會,他便利用晚年彌補這一缺憾。他對賺錢的看法是:每個社會,每個曆史階段,肯定有某些行業能賺錢;有人喜歡做律師,有人喜歡搞科研。律師收入高,但風險也很大,教師相對清貧,卻有休假搞課題,很充實;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讓我當律師,現在可能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我一點不後悔,因為我寫書比當律師更合适。
那個冬日,西北風大作,一位老者瑟縮在教學主樓的角落裡避風,寒風吹透了他身上的中山裝,他用力圍緊薄薄的圍巾,他的身體像一片樹葉将要被狂風吹起。從身邊跑過的青年大學生們不知道,這位瘦弱的老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國家和學校的重點保護“文物”、國寶級教授沈達明先生。法學院本來提出給他派車,可他執意不願麻煩學校,說坐公共汽車很方便。他家搬到望京後,他經常自己踉跄着,乘公共汽車往返,沒有絲毫抱怨。他說:“比起學校派車,我覺得還是自己坐公共汽車更方便些。”
耄耋之年的沈先生,在學術思想的活躍程度上卻是最現代、最“時髦”的。被這份甯靜的充實感包圍着,物質要求退居次要了。走進他的家,你會有一種回到了五、六十年代的感覺。他不看電視為的是不給眼睛增加太大的負擔,以便更多的用于讀書寫書。
國際經濟法專業博士點是我校的驕傲;而博士生導師沈達明教授更被視為學校的光榮。近二十年來,從國際經濟法專業畢業的本科生、研究生中,如今不乏才華橫溢的名律師、仲裁員、大學者,他們每個人身後都留下一串輝煌的足迹;然而,當這些法律界“牛氣”的少壯派們面對恩師沈達明時,他們的敏銳、機智和雄辯,就象壯闊洶湧的江河之濤,彙入了寬廣而深邃的蒼海,回歸到一種平和與甯靜。這甯靜之源,需追溯到久遠的那個時代,裡面飽含了民族滄桑沉澱的厚實養料。
就學者來說,甯靜,是一種治學的應有心态。然而,在今天商品經濟大潮下,保持心靈的這種境界已非易事。沈達明先生的甯靜卻是六十多年始終如一,不論是動蕩年月的政治風雨侵襲,還是開放時代金錢的誘惑,他保存了這份心靈空間的甯靜,而且完好無損,那是一層脫盡一切浮華的濃濃的生命底色。
![]()

圖為1985年冬,國際經濟法系教師與85級研究生聯歡。左二為沈達明教授,右三為孫維炎校長,左三為王林生副校長,右二為系主任馮大同教授,左一為系副主任陸志芳老師,右一為研究生潘琪;中間吹笛者為外籍商法課老師、美籍華人趙宏勳博士。
作者:丁激中,筆名紫丁

